虛無很主要
作者:布萊特·戴維斯 著 吳萬偉 譯
來源:譯者授權儒家網發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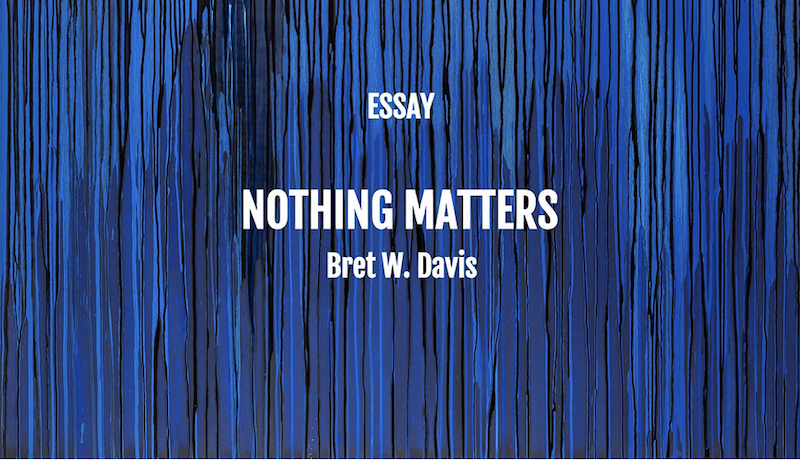
喬安娜·波考斯卡(Joanna Borkowska)的藝術品。
虛無主義的本質或許在于沒有嚴肅對待虛無問題。—馬丁·海德格爾
你有沒有一覺醒來覺得起床沒有任何意義,因為畢竟什么都不主要。或許你有這種感覺,可是,你的親身經歷或許只是將其當作一種感覺,當作某種包養一個月需求應對的主觀心思狀態,而非有關這個世界的客觀事實。你或許想到假設你強迫本身起床,穿好衣服,短期包養喝一本咖啡,促往散漫步,你將擺脫這種蹩腳的情緒,從頭投進到周圍世界有興趣義的奔走之中。
可是,你親身經歷過不僅僅是一種感觸感染的無意義性嗎?你能否醒來沉醉在無意義的迷霧之中,就似乎一張毯子把地球裹得嚴嚴實實。一種同質性的、瑣屑無聊構成的氛圍—彌漫在你的內心也包圍在你的身邊—它是多孔的,卻是壓倒一切的,既有壓迫性的繁重,又有讓人沒有方向的輕飄飄之感,這種氛圍給客觀事物以及內心思惟統統籠罩上一層無色無味的無意義感,帶著某種看似無法轉變的信心,即沒有任何東西是真正主要的,這個宇宙畢竟既沒有韻律也沒有來由,既沒有價值也沒有目標。你能否信任,我們的人生故事就像莎士比亞的《麥克白》所說,“人生如癡人說夢,充滿著喧嘩與騷動,卻沒有任何意義”?
這樣的虛無親身經歷或許總是縈繞在人類的心頭。可是,一切包養甜心網文明都在某種水平上戰勝了它。的確,文明作為培養有興趣義的規范和有目標的工程的活動—可以被懂得為一種集體的盡力,旨在戰勝潛在的無意義感,即認定一切都毫無意義,是一種語義上的“恐懼留白”(horror vacui)或許虛空恐懼癥(kenophobia)。可是,在歐洲歷史的某個點上—準確地說是在19世紀最后的幾十年里—-這種無意義感帶著難以克制的報復欲看浮下臺面,並且獲得了一種名稱:虛無主義。
是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在1885-86的一則日記中宣稱,或許至多準備好宣稱:“虛無主義站在門口。”他認為,20世紀的門檻將面對虛無開放,也就是說,人們將親身經歷到一種虛無主義,迎接“價值、意義和愿看的徹底拒絕和排擠。”人們越來越多地感觸感染到,似乎任何工作都不再主要,都沒有價值或許意義了,都不值得尋求也不值得鄙視了。尼采在1887年的另一則日記中問到“虛無主義意味著什么?”他答覆說,“最高貴的價值開始貶低本身的價值。目標已經缺掉;“為什么”找不到謎底了。”在尼采看來,基督教文明把本身玩砸了:我們對基督教的崇奉教導我們尊敬真諦,真諦則產生了科學;科學或許應該說科學主義,即科學自己能夠為我們供給有關現實的一切真諦的觀念—毀失落了我們對基督教及其價值觀的崇奉。尼采說,我們應該為“天主的逝世亡”負責。這意味著我們已經“將地球和太陽的連接切斷。”他的主張是現代東方人—除了某些反動的守舊派以外(當然在american比在歐洲還多得多)—不再真正信任我們人生所依賴的品德和意義超驗性的廣泛源頭。可是,我們不了解我們做錯了什么:我們的神學弒父者表白,不僅僅我們的罪惡再也沒有辦法獲得寬恕,並且“罪惡”和“救贖”的概念自己都已經喪掉了威力,“包養感情善”和“惡”假如不帶有神權政治上的懲罰威脅和家長制的獎勵諾言的話,將不再帶有任何意義。我們為什么還要做或許不做任何事呢?
尼采了解,他來得太早了。年夜哲學家或許總是領先于他們的時代。尼采的書在他還活著之時就已經惹起轟動,但并沒有在哲學家中帶來最基礎性的變化。不過,幾十年之后,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年夜戰之后,一些東方哲學家—包含20世紀影響力最年夜的哲學家之一馬丁·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以本身的方法對尼采的預言以及他的主題—做出回應。尼采的預言是虛無主義的到來,其主題是虛無主義無法通過逃離或許退卻來解決,而只能通過置身于“在徹底經歷虛無性的‘危險’中才幹被戰勝”,這是德國詩人弗里德里希·荷爾德林(Friedrich Hölderlin)的用語。
在他有名的—或許依照邏輯實證主義者如魯道夫·卡爾納普(Rudolf Carnap)的說法“名譽掃地的”演講中,海德格爾1929年在弗萊堡年夜學發表的就職演講“什么是形而上學?”中對學界同仁闡明了他的見解。在說明了眾多“科學”(或許“學界學科”,翻譯成更普通性的說法“Wissenschaften”能夠更好)人文學科(Geisteswissenschaften),還有天然科學(Naturwissenschaften)和社會科學(Sozialwissenschaften)之后,海德格爾問道,“當科學成為我們的豪情之后,我們的存在從最基礎上說發生了什么?”換句話說,我們能夠說,當所謂的沒有好處糾葛的尋求客觀知識代替了哲學上的愛聰明之后,具有反諷意味的是,當一種要肅清一切豪情的欲看成為安排我們思惟和實證摸索的獨一欲看時,將發生什么?各種各樣的科學考核存在的這個或那個具體領域:化學構成、生物動物、心思心智、社會群體等等。科學關心每一種存在—除了這些存在之外,其他都不關心。畢竟,除了這些存在,還有其他什么東西呢?虛無。海德格爾的聽眾或許這樣想,“到現在為止,一切都好,只是一個哲學家的某些尋常的、無傷年夜雅的三言兩語罷了。”可是,他們的下顎能夠要驚訝得失落下來了,至多眉毛要抬起來了,當海德格爾接著詢問,“關于這個虛無,該怎么辦呢?”人們能夠想象的一個反應:“這不就是一個蹩腳的語法笑話嗎?你最基礎就沒有辦法考核虛無,因為沒有東西讓你考核啊。”“畢竟沒有一個東西在那里等著你往考核。”海德格爾或許回應說,“不,那不是我們盼望的東西,”回應能夠是這樣的。房間里的邏輯實證主義者能夠年夜聲質問,“你只是在玩文字游戲。這樣笨拙的問題,其基礎除了復雜的文字游戲之外,什么都沒有。”它們與嚴肅的哲學摸索沒有任何關系;就是維特根斯坦(Wittgenstein)所說的“語言往度假”的案例罷了。海德格爾師長教師不過是別的一只需求從捕蠅瓶中飛出往的哲學蒼蠅罷了,需求逃出本身制造出來的修辭圈套。這就是為什么你們不應該給這種非科學的虛假哲學家終身傳授崗位的來由,至多在他們學會產生可權衡的學術結果之前,正如一切真正的科學學者都在做的那樣。(事實上,與卡爾納普和后來擁抱科學主義的剖包養留言板析哲學后繼者比擬,維特根斯坦自己卻很是同情海德格爾的問題,可是,那是別的一個問題。別的一個惹人進勝的故事觸及到這個事實,雖然有巴門尼德(Parmenides)的不要墮入不成言喻的和不成懂得的“非存在途徑”和亞里士多德的名言“天然界里是沒有真空的”等現代正告的漫長陰影,可是理論物理學家們越來越多地發現各種虛無觀念恰好位于天然科學最困難的難題的焦點。請參閱不僅僅是菲杰弗·卡普拉(Fritjof Capra)的先驅性的、融會性的著作—也許存在一些問題—《物理學之道:現代物理學與東方奧秘主義的平行線摸索》,並且還有約翰·巴洛(John D. Barrow)的《虛無之書:真空、空虛和宇宙來源的最新觀點》和赫寧·根茨(Henning Genz)的《虛無:虛空空間科學》。在15世紀的時候,多才多藝的里奧納多·達芬奇(Leonardo da Vinci)就宣稱:“在我們發現的最偉年夜事物之中,虛無的存在是最偉年夜的發現。”)
當然,海德格爾預料到人們能夠驚訝得失落落下巴。其實,他的意圖是飾演哲學牛虻的腳色,戳中他的那些過于甦醒的同業的雙眼,因為他們樂此不疲地但是短視地向下盯著本身瓶子里可科學測量的存在。“虛無—在科學的眼中,除了覺得是憤怒和幻覺之外,還能是什么別的東西?”科學并不盼望認識虛無中的任何東西。海德格爾很是樂意承認,對于虛無的合適邏輯的調查是形而上學的最基礎性問題,形而上學(他在該演講中應用這個詞想表達的意思)是人類存在的最基礎性特征。他也承認動腦筋思慮自己是沒有辦法對付這個問題的:“因為思慮從最基礎上說總是思慮某些東西,必須采取一種行動,這與他在想到虛無時的情況截然相反。”
作為擁有視野潛能的存在,缺少光明難道不克不及引發我們親身經歷一種無法看見卻在有時候明明感觸感染到的壓倒一切的暗中的存在嗎?
科學的合適邏輯的實證性的思慮方法總是基于特別親身經歷;任何親身經歷似乎都是對某物的親身經歷,對某個存在的親身經歷,無論是意識對象還是思惟或許想象中的觀念。怎么能夠有虛無的親身經歷呢?柏拉圖教導我們說,就像我們通過太陽光看到可感覺的物品一樣,我們需求依附感性之光看到可懂得的物品。可是,正如意年夜利哲學家吉奧喬·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在討論亞里士多德有關“潛能性”特別存在的話語(潛能性是一種希奇的“某物”,還不是實際的存在,或許從來不會存在)時指出的那樣,難道沒有一個怪異的、可是無可辯駁的意識,在此中我們的確“看見暗中”?作為擁有視野潛能的存在,缺少光明難道不克不及引發我們親身經歷一種無法看見卻在有時候明明感觸感染到的壓倒一切的暗中的存在嗎?
與此類似,海德格爾認定,我們的確擁有一種特定在場的親身經歷,這種在場指的是缺少一種有關棲身著決定性存在的有興趣義的世界。起首,他指出,我們擁有廣泛存在的情緒的某些親身經歷,里面包括了豐富的情感,引導我們往適應這個“作為整體的存在”世界,而不僅僅是存在的聚集(this ensemble of beings)中的這個或許那個存在。他說起快樂、愛情和深度無聊作為例子。好比,當你親身經歷到快樂的時候,整個世界似乎都是興高采烈的。當你覺得深度無聊的時候,一團“令人梗塞的迷霧”籠罩在這個世界上,用其“了不得的冷淡”覆蓋了一切。
可是,即使是深度無聊,這種無所不在的冷淡并不克不及充足向我們裸露出虛無性的徹底深淵。在無聊中,依然有一種有興趣義的后嘗(aftertaste)和先嘗(foretaste)—裡面實際上存在一個風趣的世包養心得界,只不過此刻我不克不及接近它,就是這樣一種感觸感染。可是,在親身經歷海德格爾所說的“最最基礎性的焦慮情緒”時,就連進進一個生成有包養俱樂部興趣義的世界的這條性命線也被切斷了。他對比了他用焦慮表達的意思“畏”(Angst)和恐懼(fear)的分歧。當我們懼怕的時候,總是對某物覺得懼怕。這個某物在我們看來有些嚇人。我們周圍的整個世界或許看起來更嚇人,就像現實版的可怕電影;可是,它依然是一個有興趣義的世界,帶著清楚的價值觀(追殺我的兇手是個惡魔)和獨特的目標(我需求趕緊逃出這個鬧鬼的屋子!)
相反,在最基礎性的焦慮情緒中,沒有任何東西看起來是有興趣義的。其實,似乎什么都沒有。事物假如要呈現出是這個樣子而不是那個樣子,或許這個緊挨著那個,那就必須存在某種意義結構。一個存在要存在,它就必須能夠被確定、被定義、被劃定邊界(接近詞源學意義上的同義詞),以便和相反的、臨近的或許某種相關的存在區別開來。存在從定義上說是彼此關聯在一路的,它們必定是在某個可懂得的語義結構內彼此聯系在一路。可是,假如這個世界不再顯得有興趣義的話,將發生什么呢?當這個世界作為語言結構的有興趣義整體已經被打破,成為彼此沒有關聯的東西漂浮在沒有結構的空間里的一團亂麻,又將發生什么呢?海德格爾說,我們將在極真個焦慮情緒中面對面遭受虛無。“一切的事物,還有我們本身都墮入冷淡無情之中。我們抓不住任何東西。在存在者統統溜走的這個過程中,只要這個“抓不住的東西”來到我們身邊,并留了下來。”
當這個世界作為語言結構的有興趣義整體已經被打破,成為彼此沒有關聯的東西漂浮在沒有結構的空間里的一團亂麻,又將發生什么呢?
薩特(Sartre)在1938年的小說《惡心》中,重要人物描寫了他遭受堅果樹糾纏在一路的樹根和公園中越來越難以捉住的東西,那些東西開始通過流淌的詞匯和概念顯示出其單純的實然存在(is-ness),我們就是用這些詞匯和概念維持捉住它們,與此同時又與它們堅持必定的距離。在這個沒有詞語的、赤裸的存在的年夜片區域中,這般沒有詞語,龐年夜的赤裸的存在,在這個多孔的、單純存在的集體中,什么東西都沒有興趣義,什么東西都不再真正主要。薩特描寫的這個親身經歷不是與虛無(在缺少存在的這個意義上)的遭受,而是遭受了存在的大批的、無法測量的、因此也是惡心的泛濫—大批拒絕被包括進往,拒絕被放進我們分派給它們的語言或概念盒子里往而變成可治理的東西。后來,薩特在1943年的《存在與虛無》中論證說,恰是人類意識的主觀性將否認性引進這個世界。否認的威力不僅意味著一種在事物之間做出有興趣義的區分的才能包養sd(這就是 f 那個,正如此賓諾莎指出的那樣,“一切規建都能否定”(determinatio est negatio)。它也意味著有才能想象世界紛歧樣的情況,因此擁有幻想能夠讓行動找到定位,旨在改變現狀朝著幻想邁進。可懂得性和創造性都請求否認性。一個完整充滿了存在的世界,一個沒有任何鴻溝和虛無泛濫的世界,并不是真正的世界,即有次序的整體這個意義上的真正的世界。它不過是多孔的、波動的小斑點,既沒有可懂得的意義也沒有現實的不受拘束,既沒有創造性也沒有責任。
伊曼努爾·列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呼應薩特的無意義存在親身經歷的描寫—單純的無意義實然(is-ness)—在1946年一篇題目為“存在:沒有存在物的存在”的文章中,列維納斯寫到“當事物的情勢在夜晚中消失,這個虛無不是那個純粹的虛空。不再有這個或那個,不是有某個‘事物’”。可是,這個廣泛的出席反過來成為一種在場,就像掉眠的時候下降在我們身上的那種單調的在場。雖然列維納斯宣稱“反對將夜晚的可怕對應海德格爾式的焦慮,或許將存在恐懼和虛無恐懼對立起來。”我們將看到,海德格爾應用存在和虛無指東西的時候是將兩者連接起來而不是構成對抗。海德格爾也沒有考慮他用焦慮作為對某物—我們需求獲得救贖的某個東西的恐懼表達的意思是什么。在海德格爾看來,我們需求虛無親身經歷,以便參加到一種存在活動之中,它將給我們的個體和集體生涯賦予意義。相反,對于列維納斯來說,是別的一個人的面貌的親身經歷和通過那張臉折射的天主的超驗性的無限性打破了存在的無意義的單調重復,用其別人的改變和我們對他們無法窮盡的倫理責任打破了本體論整體性令人梗塞的同質性。(請參閱1961年的《整體性和無限性》Totality and Infinity)
雖然列維納斯用倫理學取代本體論作為第一個哲學的先鋒派激進性,但他對存在的無意義性的回應在關鍵意義上是顯著的傳統觀點:尋求宗教超驗性的形而上學欲看和來自神圣號包養網站令的相伴產生的倫理責任(列維納斯令人佩服地描寫的是,通過別的一個人的面貌的親身經歷而最強無力地傳達出來。)形而上學超驗性為本來無意義的內活著界賦予了意義,通過別的一個人的面貌實現的神的啟示開啟了存在整體性的均質化過程。是以,列維納斯的倫理現象學用后現代術語重復了前現代的主題:超驗性的神圣痕跡為我們獲得了世俗生涯的價值觀和目標。
可是,對于尼采來說,恰是形而上學和宗教超驗性起首誕生了虛無主義。通過將世界區分紅為物質世界和超驗性世界,地上和天國,通過將這個世界的價值觀轉移到別的一個世界,通過將人生目標推遲到來世,一旦我們發現本身不再能夠維持對另一個世界的崇奉,也就是說,一旦我們有一天醒包養網車馬費來忽然發現“天主逝世了”,我們將不僅貶低了此世的生涯並且讓我們本身喪掉了任何意義和價值的源頭。我們應該為天主之逝世承擔責任,我們以真諦和不受拘束的名義殺逝世了天主;可是,沒有了天主,我們顯然不再有任何終極的源頭和確保我們生涯的品德和意義的基礎。
可是,對于尼采來說,恰是形而上學和宗教超驗性起首誕生了虛無主義。
japan(日本)禪宗釋教和跨文明哲學家西谷啟治(Nishitani Keiji)清楚,尼采宣稱的即將再度出現的虛無主義,在倫理學和宗教層次上的虛無主義就像病毒一樣獲得了抗藥性。在一份自傳性的隨筆中,西谷啟治寫到,“虛無主義是虛無性在宗教維度上的再度出現,也就是說,在虛無性凡是可以被戰勝的同樣高或許同樣深的那個維度上。”在過往,每當人們醒來墮入一種無意義性的情緒之中,或許被塵世生涯沒有終極價值和目標的意識熬煎得疲憊不勝時,他們總是能夠乞助于對更高領域的崇奉,乞助于宗教教條和神的號令,從而再度確認這種生涯—或許至多作為通向他處的一個步驟。可是,當我們不再信任神圣號令或許來世的賞罰,將會發生什么呢?我們是墮入絕看之中還是以某種方法找到發現或許創造價值觀的新方法?
假如這就是我們能夠獲得的東西,我們能夠確認我們認識的那種生涯?我們愿意一遍一遍從頭過這種生涯,連同生涯中的起升沉伏,連同一切的苦楚和歡樂,一切的歡喜和悲傷時刻?包養網推薦在尼采看來,這種“永恒性回歸”的設法的“最年夜份量”是來辨認出此人是人生確定者還是人生否認者的一種試金石。他想到,在虛無主義時代,人生否認者注定要成為盼望非存在的“消極的虛無主義者”。另一方面,人生確定者能夠成為“積極的虛無主義者”,即摧毀陳舊價值觀的殘余,以便他們能為創造新價值觀開辟途徑。這種積極虛無主義者為“超人”(overman),一種進化水平更高的人開辟了途徑。從這種人身下流出來的“權力意志”能夠讓他創造本身的價值觀而不是臣服于被“禁欲的牧師”刻在石頭上的圣徒,這些人被認定為至高無上的主的助理。
年輕的西谷啟治遭到尼采的影響很深,到了中年時期,他把1949年出書的著作《虛無主義》(在作者的批準下,標題被翻譯成《虛無主義的自我戰勝》)的焦點章節都拿來闡述對他對尼采思惟的發人深省的深入解讀。可是,到了他1962年出書代表作《宗教是什么》(在作者的批準下,標題被翻譯成《宗教和虛無》)時,西谷啟治對尼采的權力意志哲學的批評力度變得越來越強。他逐漸將權力意志視為釋教所說的因果報應—羯磨(梵語:karma),自我主義的自我意志或許確保我們綁定在一種生涯方法上的“無限的驅動力”,這種生涯方法讓我們的無知和苦楚永遠存在。尼采誤解了釋教,將“進進虛無的意志”看作是消極虛無主義的頂點,那是一種終結一切欲看和消散在涅槃的空蕩蕩的虛無之中的自我毀滅欲看,同樣,西谷啟治則依照年夜乘釋教(Mahayana Buddhist)(包養站長尤其是禪宗)的適當方法把涅槃懂得為自我主義尋求的火焰的熄滅,這種尋求讓人從一種產生苦楚的生涯方法中解脫出來,進進一種博愛、慈善和充滿同情和快樂的生涯方法。
就像禪宗年夜師早就教導我們的那樣,我們必須經歷存在性的年夜逝世以便實現年夜活。
除了尼采的著作,傳統禪宗年夜師好比18世紀的japan(日本)禪宗年夜師白隱慧鶴(Hakuin)和現代japan(日本)作家如夏目漱石(Natsume Sōseki),西谷啟治一向以來都在摸索最深入的現代基督教作家如陀思妥耶夫斯基(Do包養情婦stoyevsky)和最激進的中世紀奧秘主義者和否認性的德國神學家、哲學家和奧秘主義者埃克哈特年夜師(Meister Eckhart)的著作,此人留意到有時候談及天主性的“緘默的荒涼”—位于天主圣父之外或許之下—-作為“虛無”的深淵底部。西谷啟治起初感觸感染到在埃克哈特的徹底有神論和尼采的徹底無神論(或許依照內在的狄俄尼索斯術語(Dionysian terms)徹底從頭考慮神圣性)之間的一種奧秘的契合性。在其第一本書的第一章,基于他20世紀30年月末期棲身在弗萊堡時寫成并提交給海德格爾的一篇論文中,西谷啟治用的“人生辯證法”的術語說到了這種契合性。在這種辯證法中,人類能夠通過激進否認的方法來實現一種對激進人生的確認。就像禪宗年夜師早就教導我們的那樣,我們必須經歷存在性的年夜逝世以便實現年夜活。用現代窘境的說法,在西谷啟治看來,這意味著我們能夠“通過完整經歷虛無主義來戰勝虛無主義”,他應用這樣的術語逐漸描寫他的思惟和人生途徑。
在《宗教和虛無》中,西谷啟治借用釋教(尤其是禪宗)術語來解釋這個過程,應用從具體化(reified)的“存在領域和(代表性)意識”通過“虛無領域(the field of nihility)”“后退幾步”一向到“虛空領域(the field of emptiness)”。雖然空虛領域(kū no ba空の場所)是通過虛無性領域(kyomu no ba虛無(k包養感情yomu)の場所)的激進化而達成的,他說,總體上分歧于這個否認性的虛無:“是這個立場,絕對否認同時也是偉年夜的確認。”這里的空虛不是從存在一邊看見的“相對性虛無”,作為來本身外的攻擊的某種東西,而是從內部看見的“絕對性虛無”;恰是在對面的到來作為像絕對近面的回歸。雖然列維納斯談到朝向天主的絕對他異性的形而上學“超驗性包養軟體”,西谷啟治談及的“超驗性”則是激進地后退幾步進進空虛領域作為自我的“起點”,這是一個領域一切的存在被實現成為它們真正成為的東西:“本身存在”(own-being)的空虛或許獨立的實體,但充滿了彼此存在(inter-existence)或許“彼此蘊涵(mutual implication)”。作為我們醒來意識到我們的最後彼此聯系的實驗領域,空虛領域是“絕對的近面”(zettai shigan絕対)。那是愛情和慈善天然從內部和我們中間產生的一個領域,無需誡命—也無需來自上邊的承諾、獎勵或許懲罰的威脅。
在其1937-1939年間在弗萊堡的短暫逗留期間,西谷啟治據說獲得了長期的邀請,要在周末前去海德格爾的家為其講授禪宗。海德格爾終身對東亞思惟的濃厚興趣獲得了傑出的記錄。他經常表達出的不僅是對道家和禪宗釋教濃厚的興趣,並且還有強烈的同情。在其解構整個東方哲學傳統背后的形而上學基礎的嘗試中,海德格爾經常發現他要表達的后形而上學思惟的其他開端與東亞思惟的現代傳統構成共鳴。(在多年夜水平上這些共鳴是偶合還是影響,這依然是學界爭論不休的話題。)
海德格爾有時候說,對他的思惟領會得更深入的是東亞人而不是其東方人同胞。在誤解他的東方人中,海德格爾想到的不僅是指控他滿嘴胡話的人如卡爾納普(Carnap),並且還有充滿熱情地修正其思惟的人如薩特。海德格爾在1945年戰爭結束后不久,曾經獲贈一本《存在與虛無》。在此時寫給薩特的信中,海德格爾表達了他的熱情,稱贊薩特踏上了他在1927年的《存在與時間》中開辟的途徑。(面對當時的往納粹化聽證會,海德格爾顯然也很是感興趣能贏得有名法國知識分子的支撐。)可是,在其1947年“關于人性主義的書信”中,這是一篇內容濃密的文本,通過批評薩特的“存在主義是一種人性主義”很是隱蔽地介紹了海德格爾思惟上的嚴重轉變,海德格爾決定性地和薩特的人性主義存在主義的自愿主義(voluntarism)決心堅持距離,在這種觀點看來,人是“他盼望本身成為的那種人。”在薩特看來,人最後“出現在這個場合,”發現他存在于一個特別的處境中,擁有向它開放的特別范圍的能夠性,可是包養條件,在那個處境中,他基于薩特宣稱的“意志”的“自發性選擇”繼續在最基礎上“定義自我”。
肆意性地給世界添加意義的盡力最終導致的是強化了這樣一種印象,即這個世界自己是沒有興趣義的。
海德格爾對薩特的主觀自愿主義的冒昧無禮的拒絕應該被放在他自己長達10年的納粹哲學對抗的佈景下對待。海德格爾逐漸認為,假設權力意志是存在者的存在(the being of beings)不過是顛倒的形而上學。海德格爾已經逐漸認為,任何情勢的自愿主義都無法供給一種擺脫虛無主義的靠得住方式—無論是有神論還是無神論,無論是個體的還是群體的,無論是尼采的,薩特的,或許海德格爾本身在《存在與時間》中更早的個人主義的決策主義(individualistic decisionism)或許他后來宣稱台灣包養網的他在20世紀30年月初期信心的“宏大笨拙”,即信任希特勒體現出“德意志平易近族的單一意志”。相反,任何類別的自愿主義都表白“最深入地卷進虛無主義的深淵,”因為肆意性地給世界添加意義的盡力最終導致的是強化了這樣一種印象,這個世界自己是沒有興趣義的。意義基于一種難以深究的肆意性的自我中間主義的、種族中間主義的、人類中間主義的、或許擬人化包養網單次的神學中間意志。
在尼采宣稱“這個世界是權力意志—除此之外,再無其他”之地,海德格爾認為,權力意志是從歷史上看的存在者的存在的劃定邊界的懂得。他事實上提出疑問,“這個除此之外再無其他”是什么?存在和虛無還能若何用別的方法來懂得?海德格爾認為,薩特也簡單地顛覆了東方形而上學的術語;他在嘗試隨意掙脫它們束縛的意思時,甚至比尼采還更少些。好比,海德格爾認為,薩特的無神論人性主義是對有神論的匆倉促拒絕,這種有神論簡單地用渺小的情勢將神的特質轉移到人身上。代替了神從原始的汪洋一片中創造一個有次序的宇宙(正如《創世記》實際上說的話,雖然這個圣經宇宙學后來被基督教神學家們進行了很年夜水平的修正,他們提出了從虛無中創造(creatio ex nihilo)的教義,這種神學教義和現代哲學原則“無中不克不及生有”(ex nihilo nihil fit)異曲同工。對于零(nihil)的解釋,就是作為存在的出席。對于薩特來說,恰是人類意識和意志的“為了自我”將意義強制性地放在存在的無意義的“安閒”(the “in-itself”)上。同樣,海德格爾認為,薩特誤解了他在《存在與時間》中的命題,“此在的本質就在于其存在。”薩特簡單地顛倒傳統的形而上學觀念本質先于存在,海德格爾則嘗試同時思慮本質與存在。在海德格爾看來,存在是一種“被攜帶進進虛無”的問題,這是他在“形而上學是什么”中說的話。在其“關于人性主義的書信”對薩特的批評中,海德格爾進一個步驟廓清了他的意思,存在是“在存在真諦中的心醉神迷的固有性。”人類的存在,即此在(Da-sein (there-bein包養甜心g))是開放的處所或許澄明(Lichtung),此中存在逐漸擁有了有興女大生包養俱樂部趣義的在場。在海德格爾后期看來,人類并沒有肆意地投射存在的意義,而長短常非肆意性地參與到“語言在言說”(die Sprache spricht)的事務中,為人類的存在打開了從語言上說有興趣義的空間。在從頭思慮“存在”作為人類被召喚往親密關注和參與的“適當事務”中,海德格爾懂得這個我們被拋進的“虛無”,在我們生涯中最真實和最具創造性的時刻,作為新意義能夠性的一個條件,而不僅僅是僵化的、陳舊意義的消解。
在“關于人性主義的書信”中,海德格爾的確接收了導致其思惟被誤解的某些責任,因為他承認本身依然在處于擺脫東方形而上學語言束縛的掙扎之中。一個說明問題的例子是,海德格爾用虛無的概念思慮存在。雖然這在東方人看來不成能不覺得迷惑不解,雖然在邏輯上他們很嚴謹,並且有簡單地將存在與虛無對立起來的本體論,可是,因為東亞人將虛無僅僅懂得為存在的否認或許喪掉,海德格爾認為,他們處于更好的地位來懂得他試圖思慮和準備說的話。
在若干場合,海德格爾說japan(日本)人能夠比歐洲人同胞更好地輿解他用“虛無”表達的意思。海德格爾在1963年寫給一位japan(日本)學者的信中說,
“什么是形而上學?”這篇演講早在20世紀30年月就被翻譯成日語,並且很快在你的國家被懂得,這與它引進的這些術語的虛無主義誤解在歐洲直到明天依然占上風的情況構成明顯對比。在演講中和存在(das Seiende)對應,被稱為虛無(das Nichts)的東西從來不是任何一種存在(niemals etwas Seiendes),它是以“是”虛無,可是依然決定了這樣的存在,是以被稱為“此在”(das Sein)。
在1969年寫給德國同事的信中,海德格爾寫到,“在‘虛無’獲得適當懂得的遠東,人們在這個詞中發現了存在。”在他的基于他和一位來自japan(日本)的訪問學者的對話而寫成的“來自關于語言的對話(1953/54):一個japan(日本)人和一個摸索者”中,海德格爾表達了對japan(日本)人懂得其焦點思惟—存在作為虛無的才能的高度贊賞,他的japan(日本)對話者宣稱,“對我們來說,虛空是最高貴的名稱,指你用‘存在”這個詞表達的意思。”其實,真實的情況或許是japan(日本)哲學家好比西谷啟治有時候懂得海德格爾想表達的意思,甚至比他自己懂得得更好。好比在《宗教和虛無》中,西谷啟治質疑,在說到“存在被拋進虛無時”,海德格爾事實上依然在將虛無客體化,變成站在我們眼前的某種東西。
依照西谷啟治的說法,就海德格爾想到的虛無作為此在被拋進一種焦慮狀態的深淵,“虛無作為某種“物”(從裡面給此在帶來威脅)的代表的痕跡依然存在。”西谷啟治在京都學派的后繼者上田閑照(Ueda Shizuteru)追蹤了海德格爾本身對我們與虛無的關系的懂得的演變軌跡。海德格爾已經在“什么是形而上學?”中談到了焦慮之中的“怪異的平靜”,說“那些年夜膽者的焦慮”事實上“是創造性盼望的歡快和溫和的機密聯盟者。”上田閑照暗示,海德格爾在那個晚期演講的結尾處提到的“釋放本身(Sichloslassen)進進虛無”在海德格爾的后期思惟中“獲得激進化,變成了一種恬然處之(Gelassenheit)觀念。”恬然處之(Gelassenheit)這個詞是埃克哈特年夜師創造出來的,被基督教奧秘主義者用來談及放棄自我意志而產生的“平靜釋放”,被后期的海德格爾修正后用來描寫我們最適當的存在(或許虛無)方法的成分特征。此中,我們從意志的現代形而上學中釋放出來,往包養犯法嗎迎接一種存在的開放空間(Gegnet)的奧秘親身經歷,這種存在圍繞在確定存在棲身的我們有興趣義的世界的劃定邊界的視野周圍。通過將我們人類中間主義的意志束縛中束縛出來,進進科學懂得的和技術把持下的無限存在領域,我們釋放本身進進一種虛無親身經歷,作為被掩蓋起來的佈景,存在的寬闊開放空間的過分內斂和收縮,一種難以計算的揭穿事物能夠性的寶庫。在他的學術生活中,為了強化他所說的“本體論差異”,也就是存在者的存在和存在物的差異,海德格爾有時候將存在說成是虛無。存在不是一個存在物,一個實體,是以,它是無物(no-thing)。在他的最緊湊、最晦澀難解因此奧秘莫測的描寫之一中,海德格爾寫到,“存在:虛無:一回事”。可是,海德格爾用“一回事”并沒有預計說存在和虛無是單純的同義詞,而是說它們難以解釋明白地屬于一個整體,就像統一枚硬幣的正反兩面。雖然他在分歧的佈景下提到這種親密關系的方法分歧,普通來說,可以說的是,在海德格爾看來,虛無是總是伴隨著存在的隱晦(unconcealedness)的掩蓋。虛無在本質上是存在的一種自我收斂或自我掩蓋的維度。它是無蔽的掩蔽(the lethe of aletheia),適應事務“發生”(Ereignis)中卷進的修正“自行歸隱”(Enteignis),圍繞在(澄明(Lichtung))任何有邊界的開放性黑叢林的奧秘(Geheimnis),那是可懂得性的光線能夠照亮之地。它不是匱乏或空虛,而是劃定邊界的開放領域的完全性,此中這個或許那個劃定邊界的存在意識—這個或許那個意義視域—逐漸開始構成。
道家懂得道即途徑的方法是不確定的可是生殖力茂盛的虛無或許虛空,它能產生和容納確定性的存在。
在海德格爾看來,虛無不是存在的虛無主義的匱乏,相反,正如他在《哲學的貢獻》中所寫,“虛無是存在(beyng [現代表現存在的單詞,Sein的陳舊拼寫] 的本質性顫抖,是以比任何其他實體更多。”為了強調存在的時間上的動態變化特征,海德格爾有時候應用它指“道”(der Weg)。他明確指出這與道家的焦點概念道有關。道家懂得道即途徑的方法是不確定的可是生殖力茂盛的虛無或許虛空,它能產生和容納確定性的存在。在道家的基礎著作《品德經》中,我們原告知“存在源于虛無(有生于無)”“道乃中空的運載東西(沖),可是,用處從來不克不及填滿其深淵性的深度。”海德格爾也提到《品德經》中的一個段落,提到了虛無在加倍明顯的劃定邊界的意義上的用處。罐子是陶土做成的,可是它的中空恰好是讓它有效的原因地點。
同樣,衡宇是由四面墻構建而成的,可是它的開放空間是讓它變得有效的原因。像《品德經》一樣,海德格爾吸引我們的留意力到虛無的這些劃定邊界和非劃定邊界的意義地點。西谷啟治的老師和京包養價格ptt都學派的創始人西田幾多郎(Nishida Kitarō)提出了一個嚴謹論證和復雜表述的哲學,焦點圍繞著一個觀念“絕對虛無的處所的自我確定性”(絕対無の場合の本身-限制)他區分了絕對虛無和“相對虛無”。前者是被懂得為一切顯示的一切現實的天生性矩陣,沒無形狀的,但是是一切自我劃定邊界的情勢的自我劃定邊界的前言,后者是被懂得為單純的存在缺掉或許客觀存在的主觀性意識的缺掉。西田幾多郎廣泛對比了東方和東方文明的形而上學條件,東方的存在凌駕于情勢之上,東方的虛無凌駕于無情勢性之上。當然,存在顯著的差異和辯論以及規則中的破例,這些在東方和東方傳統中都存在。應用了空性(nskrit: shunyata; Chinese: kong; Japanese: kū)有時候在釋教分歧派別之間產生爭論。這些釋教的虛空含義以分歧的方法和道家的分歧的“虛無”含義有關聯(漢語中是無,日語中是mu)。這些術語和教導被傳統禪宗年夜師和現代京都學派哲學家以分歧方法交織在一路。本文沒有工夫闡述這個復雜的思惟史的范圍(作為起點,我推薦劉繼龍(J. L. Liu)和伯格(D. L. Berger)編輯的文集《亞洲哲學中的虛無》和拙文“禪宗中的虛空情勢”)。我也沒有工夫更深刻對比東方奧秘主義好比埃克哈特(好比拙文“為了虛無放棄天主”)和海德格爾等哲學家(請參閱拙文“海德格爾與亞洲哲學”)。這里,請讓我簡單評論特別值得留意的一兩個匯合點,或許至多是穿插點,援用了拙文“海德格爾與道家:不用要的存在的無用之道的對話”。在第二次世界年夜戰將近結束的時候,海德格爾給老婆寫信說,“在不用要的本質(我的意思是“存在”表達的意思),我比來發現了兩位中國思惟家的簡短對話,我現在抄錄給你。”他在這封信中抄錄的對話選自《莊子》,道包養網VIP家的第二本基礎經典。年夜約在同時,海德格爾在《鄉間巷子對話》結尾段落中也援用了這個對話。這個關鍵樞紐文本恰好就是在他的思惟發展的中期創作完成的。中文里表現海德格爾所說的“不用要”(das Unnötige)的詞語“無用”凡是被翻譯成英文中的“useless”。海德格爾令人印象深入地辨認出這個觀念同等于他用“存在”(Sein)表現的意思。我們已經看見包養心得他說同等于“虛無包養網單次”(das Nichts)。《莊子》也用“虛無”或許“虛”來說到“無用”。任博克(Brook Ziporyn)將海德格爾援用的《莊子》中的這個對話翻譯如下:
惠子對莊子說,“你的話沒有效。”莊子說,“理解沒有效處,方能跟他談有效之處。年夜地既廣又年夜,人所占用的只是腳能踏到的那一個平方罷了。既然這般,那么只留下這一小塊,把其余地盤所有的挖失落,一向挖到黃泉地獄,這樣看來,年夜地對人來說,還有效嗎?”惠子說。莊子說,“那依照這個事理來看的話,沒有效處的用處天然就很清楚了。”(請參閱: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六合非不廣且年夜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廁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另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也亦明矣。”——《莊子.外物》)
我們凡是僅僅關注此刻直接在我們腳下的無限空間,也就是說只要那些在我們現有懂得視野內被認為有效的或許需要的東西。我們依照事物在這種意義框架中的地位來懂得和應用事物;依據他們在我們關心的事務處理中飾演的腳色。可是,正如莊子所說,“依附它所處的位置而被呼應或不呼應來做的事,或許依據它可巧飾演的腳色來評判包養俱樂部某物,這難道不是荒謬好笑的嗎?”“人皆知有效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人間世》)
依照《存在與時間》的晚期海德格爾觀點,我們將存在起首和重要地輿解為世界中的“設備”,也就是說處于“意義整體”之中,這個整體是由“目標”通道的鏈條構建而成的,這些通道帶領人們進進終極的“目標”(Umwillen),即一個由我們的意志(Wille)投射的人生工程。可是,在《鄉間大道對話》中,海德格爾改變了立場,從意志轉變為恬然處之(Gelassenheit)。在那里,與道家的無為觀念不謀而和,他明確提到《莊子》中被援用的段落。海德格爾強調說,假如沒有周圍尚未發現的和顯然“無用的”和“沒有需要的”的地球擴張(海德格爾的開放空間或許莊子的“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今子有年夜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莊子·逍遙游》)我們就不克不及越過現有視野,往開辟新懂得和親身經歷這個世界的新途徑。
海德格爾有一次寫到哲學的用處在于它沒有直接用處。“它只要間接的影響,在那個哲學摸索為我們的舉止行為和決策準備新視角和標準。”在此意義上,我們與對象和目標的一切科學和日常買賣,與在我們現有懂得視野內裸露出來的事物和任務,都取決于哲學的更寬廣世界觀,這種世界觀都必須習慣于無用之用。迷掉在治理明顯需要性的功名利祿的鼠奔之中,我們掩蔽了本身擁有的對“不用要性”的更深入需求。
“在存在中奔走”(Umtrieben an das Seiende)甜心花園,我們依然忘記了我們與存在(Sein)的與世隔絕以及不確定的大批無物(no-thing)的基礎關系。這些東西可以被隱喻地輿解為囊括我們棲身的“劃定邊界的林中空位”的濃密“樹林”,或許作為令人暈頭轉向的龐年夜“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此中容納了我們有興趣義的世界描寫的“視野”。晚期海德格爾很著名地將人類描寫為活著存在(being-in-the-world)。可長期包養是,在依據禪宗釋教佈景來解釋海德格爾的時候,上田說,這其實總是在雙重世界存在的問題,因為我們總是生涯在一個往除邊界的世界,它反過來位于尚未往除邊界的“虛空”((kokū),正若有限的地球能夠被描寫為無限宇宙中的棲身之所。
***
我們典範地擁有地道視野;我們只看見日常生涯常規里有次序的架構,這個架構是由我們個體和集體工程產生的,在此架構中我們在生包養網dcard涯中為功名利祿鼠奔。位于我們凡是習慣于棲身的盒子邊界之外的東西,就算出現甚至從頭出現之時也只能呈現為虛無。我們能夠親身經歷到這種虛無—假如和當我們真的親身經歷到它的話—作為對我們繁忙生涯的令人擔憂的、或許不便利的干擾,這種生涯里充滿了有興趣義的任務,它們似乎不斷請求我們全身心腸關注。我們的有興趣義的世界視野之外的開放空間,即便真的呈現出來,也只能呈現為無意義的烏有鄉,作為喧囂的、一團亂麻的一鍋粥,要么是引發焦慮的虛無主義虛空,要么是引發恐懼和擔憂的真空。
我們典範地擁有地道視野;我們只看見日常生涯常規里有次序的架構,這個架構是由我們個體和集體工程產生的,在此架構中我們在生涯中為功名利祿鼠奔。
海德格爾的名言是,“提問是思惟的虔誠。”這成為美麗時髦的哲學格言,經常被刻寫在哲學愛好者和裝腔作勢者喜歡光顧的咖啡館杯上的語錄。可是,假如我們嚴肅對待它,并開始質疑一切,它能夠顯得任何東西都不主要了,就似乎確定性的墊子被從我們腳下抽走,讓我們裸露在虛空性的無意義深淵眼前。我們或許甚至打翻了我們的無咖啡因卡布包養dcard奇諾,可是,假如我們在那個親身經歷中勾留或許逃離那個親身經歷,我們或許開始感覺到不受拘束束縛。正如海德格爾所說,當“當我們釋放自我進進虛無,我們將本身從人人都必須崇敬的那些偶像中束縛出來,我們不再愿意卑恭屈節了。”我們或許親身經歷到這種虛無,不是作為引發發急的空無一物的虛無性,而是一種寬敞的開放性,讓我們擁有不受拘束和創造空間。我們或許發現虛無的不確定性不僅僅不是虛弱無力的匱乏並且是多孔的地下噴泉,不斷冒出尚不決義的能夠性。
正如海德格爾和莊子建議的那樣,假如我們張開雙臂擁抱那個開放的空間,為爭取那個不受拘束而束縛自我—為了超出我們的占安排位置的思維形式和行為形式的那個領域的開放性,我們將發現虛無能夠成為不受拘束的空間:擺脫僵化的語言和概念限制的不受拘束,從頭思慮存在者的存在的不受拘束,從頭想象我們生涯能夠性的不受拘束,從頭規劃我們配合棲身的有興趣義的世界的變量。正如西谷啟治建議的那樣,假如我們一向后退穿過虛無性的領域,我們或許發現我們最後的家園是個虛空領域,這個發現能夠將我們從自我的和的配合體的具體化和感情依戀中束縛出來,讓我們能不受包養妹拘束地進行充滿豪情和創造性的一起配合。本文從反思令人深度擔憂的感情開始,覺得任何東西真的都不主要。假如你沒有轉過臉往,假如你堅持把文章讀完,雖然它已經更進一個步驟墮進虛無主義的深淵這個話題,假如你耐煩地思慮東亞哲學家或許比海德格爾的東方同業加倍準備好懂得他運用怪異的違背邏輯的言內行為的前進標的目的,現在你能夠清楚,結果這般,虛無真的很主要。的確,“虛無”可以被懂得為哲學家的終極關懷,這意味著在一切人中,只要我們在呼應最關鍵的和最認真負責的保存召喚。
作者簡介:布萊特戴維斯(Bret W. Davis)馬里蘭州羅耀拉年夜學(Loyola University Maryland)傳授,希金斯(T. J. Higgins, S.J. Chair)講座傳授。除了獲得范登比爾特年夜學哲學博士之外,他還在德國學習和任教一年多,在japan(日本)學習和任教13年。用英文和日文發表論文幾十篇,研討課題觸及到年夜陸哲學、亞洲哲學和跨文明哲學。譯著有海德格爾的《鄉間巷子對話》和眾多日文文本。著作和編輯的書籍包含《海德格爾和意志:走向恬然處之之路》(2007), 《japan(日本)哲學和年夜陸哲學:與京都學派對話》(2011), 《牛津japan(日本)哲學手冊》(2020), 以及《禪宗之道:哲學緒論與禪宗釋教實踐》(2022)。
譯自:”Nothing Matters”: An Essay by Bret W. Davis (Keywords: Zen; Kyoto School; Nihilism; Metaphysics) From The Philosopher, vol. 109, no. 1 (‘Nothing’).
“Nothing Matters”: An Essay by Bret W. Davis (Keywords: Zen; Kyoto School; Nihilism; Metaphysics) (thephilosopher1923.org)
本文的翻譯獲得作者的授權和幫助,特此致謝。——譯注
發佈留言